娱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娱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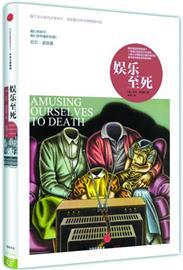
■庄加逊
这的确是大众话语蓬勃兴盛的时代,充斥着爆炸性体量的信息、娱乐化的泡沫、较为宽松的言论选择。
如今,全世界都在热议特朗普时代的到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的常客、作家约书亚·查尔斯却发表了文章,题目为——“你以为这仅是特朗普时代么?不,比这还要糟,这是尼尔·波兹曼的时代。”如此,将一本写于30多年前的书《娱乐至死》重又推回舆论的风口浪尖。
洒上点 “娱乐”才能体面
这是一本关于“娱乐”的书,很遗憾它一点也不好笑,读时叫人拍案,掩卷时又不禁气馁。它所描述的正是今天的生活,所探讨的正是当下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构成这本荒诞又真实的预言书做出了重大贡献。
《娱乐至死》是一面镜子,社会表演被雕刻进大众传媒语境中,这其中的惊愕不言而喻。何以原本仅是调味品的“娱乐”已爬上主菜的位置,成为所有议题的核心内容,如今周遭的一切似乎都要洒上点“娱乐”才能体面、自信地上桌,人们有必要跟着尼尔·波兹曼严肃地重新审视“娱乐”二字以及属于我们的娱乐时代。
尼尔·波兹曼,地道纽约客,世界著名媒介文化研究者与批评家,是继麦克卢汉之后世界最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之一。1971年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介生态学”专业,开始就所谓强势媒介进行深入探讨。虽然是麦克卢汉的忠诚信徒,但尼尔·波兹曼对于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还是作出了修正。他认为媒介可以通过改变人们传递、接纳信息的方式,进而悄无声息地改变你看待事物的角度,乃至对事物的理解。而所有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这本代表作《娱乐至死》中。
从1985年初版至今,它先后被译作八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这在不那么具有娱乐性的书籍中已算表现非凡。
原书英文的标题实为《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波兹曼以略显搞笑却酸溜溜的语气梳理了人类如何从以印刷、文字为核心的阐释时代进入以科技、碎片为核心的娱乐时代,究竟这些我们曾经奉若经典的文明硕果是怎样一步步走下神坛,进而分崩离析、灰飞烟灭的。这一回,为人类缔造舒适、完美生活的良善科技被波兹曼当作枪靶子,而作为那个时代最先进智慧的公共话语媒介代表——“电视”则被送上了审判法庭。
说起信息爆炸,我就想笑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首次触及艺术品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此时此地。由于复制技术的使用,原本躲在博物馆里的独一无二的“蒙娜丽莎”从神坛上走下来,走到普罗大众的面前。当然这可视作一种进步,然而代价是艺术品真实灵魂的消解。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将蒙娜丽莎拥入怀中,不必在乎她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年,各式各样的蒙娜丽莎经过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变成娱乐版以每天成千上百页的速度见证眼球运动的活跃度。她们需要拿自己的娱乐指数竞争那可怜的几秒,随时准备着被新出土的下一位蒙娜丽莎赶下台。
这便是娱乐时代:“此时此地”变为“一切皆是过往云烟”。正如波兹曼在书中的阐述,技术不可避免地消解了真实的客体,将一切变成断裂的碎片。作为隐喻的媒介将对内容进行改写,为了匹配相应的媒介,内容只能不断降格自己的身份。基于印刷术苦心建立起来的阐释时代坠落了,我们关心的是信息爆炸而非真实信息,我们在乎的是印象而非观点,总之,我们因抛弃语境而轻松自在。尼尔·波兹曼在书中这样写道:
如今,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是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除了了解最表面情况外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行动。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波兹曼进一步解析信息变异的过程:视觉影像取代文字成为公共话语模式的主流,这些过剩的信息被加工成更多无营养的垃圾。将视觉称作“语言”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的本质区别。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视觉是一种描述特例的语言,是断裂的描述,它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图像本身无法再现无形、遥远、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当图片替代文字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主流时,是否也在颠覆个体的思考过程进而影响观点,尼尔·波兹曼洞察到这种倾向性的恐怖。
电视通过创造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他们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到处皆是水,可是没有一口能喝。
我们在这个社区济济一堂,嚼着爆米花,愉快地聊着那些无关紧要的大事,如今也不过如此吧!
娱乐也可能成为霸权
在历数政治娱乐化、法律娱乐化、宗教娱乐化、医学娱乐化几大罪状后,尼尔·波兹曼惊世骇俗地将矛头对准著名的,甚至到今天都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教育节目《芝麻街》。很多人认为这个观点与背后支撑的信息有待推敲,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在这个话题上,波兹曼更多地认为电视教学与学校教学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教育的目的是一种试炼,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而我们的父母也常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挂在口边。教育娱乐化代表着社会文明最后的崩塌。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教育部门投资数十亿美元为每一个教室配备互联网设备,在纽约大学执教的尼尔·波兹曼暴跳如雷,质问道:“为什么要装这些东西,有什么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上网的学生就会学得比较好吗?当然不!”尼尔·波兹曼的恐惧有目共睹,他以自己的言行反复强调教育理应是持久的、艰难的,需要付出的是代价、耐力与汗水。不管如何,人们已经听够了尼尔·波兹曼的呼喊,《芝麻街》照样很流行。
你以为尼尔·波兹曼口中骇人的末世相是一种终结吗,恰恰相反,它仅仅是开始,只要将“电视”稍加替换,换作任何一种当下贴近人们生活的科技应用,比如网络、微信,文本同样成立。我们需要反复强调,波兹曼并未批判娱乐内容本身,技术进步当然有意义,私底下,娱乐依然是美妙的必不可少的消遣。我们关注的是以娱乐的方式诠释所有严肃公共话题的不利倾向,它意味着理应包含多层次、多面相的公共话语的退化。娱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娱乐。
诚然,尼尔·波兹曼的论述有其美国语境,并不适合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形态,每个社会共同体必有自己的困局。在众多复杂的关联中,科技与文化在公共话语中的矛盾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娱乐至死》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略显无力,但也是最柔软动人的地方:身为社会中人的苦恼,一种无能为力的虚弱。尼尔·波兹曼似乎已成为大众媒介里执着的西西弗斯,反复推着最终还是会掉下来的石头。《娱乐至死》的意义在于强化了问题:技术、娱乐同样有可能成为霸权,在这个意义上,奥威尔与赫胥黎的预言终于合二为一。我们真的因舒服而麻木,因麻木而放弃思考了吗?
沃尔特·李普曼说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没有反思的社会是毫无意义的,纵使我们可以把这“危言耸听”当笑谈笑上千遍,但笑过,请思考。这不仅需要一种理解,更是身为社会中人的责任。